婚礼当天,我穿着租来的婚纱站在镜子前。母亲正往我头上别最后一朵珠花,父亲在客厅清点彩礼。三个月前他们开始为这场婚礼凑钱,两个月前我才第一次见到所谓的新郎。酒席摆了三十桌,宾客们举着酒杯说恭喜,没人看见我指甲掐进掌心的血痕。
婚纱里的囚徒
化妆师夸我皮肤白,说粉色腮红衬得气色好。我看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,想起二十五年来对婚礼的幻想——应该是穿着自己选的鱼尾裙,在阳光里走向相爱的人。而现在,这套三万八租来的婚纱像套沉重的枷锁,裙撑硌得大腿生疼。

酒席上的审判
司仪在台上说着"天作之合",宾客起哄要新人喝交杯酒。我端着酒杯,看见他西装口袋里露出半截酒店房卡。母亲在第二桌抹眼泪,她说过"女人总要忍一忍"。父亲正给亲戚倒茅台,酒瓶上的红绸带像道封条,封住了我二十五年的人生。
突然有小孩打翻果汁,鲜红的液体在白色桌布上漫开。我盯着那片污渍,想起今早化妆间里,他对着电话说"晚上老地方见"。玻璃杯映出我扭曲的脸,司仪还在念着百年好合的祝词。
掀翻的不仅是桌子
当司仪喊"新娘给公婆敬茶"时,我听见自己脊椎断裂的声音。茶盘飞出去的瞬间,二十年的乖顺跟着瓷片一起碎在地上。茅台酒在波斯地毯上洇出深色痕迹,像终于流出来的眼泪。母亲尖叫着扑过来,被我扬起的头纱扫过脸颊。
婚庆公司准备的香槟塔轰然倒塌,泡沫溅在司仪擦得锃亮的皮鞋上。我扯下头纱时,珍珠崩落的声音像小时候摔碎的存钱罐。有人喊"拦住新娘",我踢掉高跟鞋冲进消防通道,消防门合上的巨响震碎了请柬上烫金的"囍"字。
三个月后的阳光
现在我在城东公寓的阳台上煮咖啡,三个月前用彩礼钱租的。楼下幼儿园正在放儿歌,比婚礼进行曲好听得多。昨天母亲来过电话,没提让我回家的事,只问新买的四件套要不要帮我晒。
晨光透过白纱帘照在左手腕上,那里有道浅浅的疤,是掀桌时被玻璃划的。我摸着凹凸的痕迹,想起酒席上那些惊愕的脸。咖啡机发出轻响,和婚礼那天的喧闹相比,此刻的安静如此真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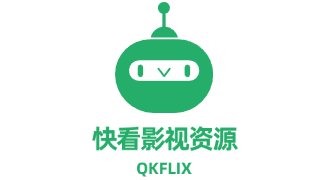



评论